《女與兒》:一部關於女人,也關於男人的獨腳戲 「當生活迫著演戲時,劇場會比寫實更真實!」
人物專訪
一個人站在舞台上獨自演戲,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惡夢,但對林珍真(Jennifer)來說,卻早已習以為常。因為對她來說,獨腳戲正是她與觀眾甚至世界溝通的方法,站在台上的她才能夠真正「做自己」;即使如Drama Queen般站在台上講女生自己的故事,也不需要覺得羞恥。為了訪問,筆者先去了金鐘廊看她的個人展覽《What she really thinks》,通過照片與文字,我自以為看到了Jennifer真實的一面,但訪問時她卻提到,最真實的自己原來是藏在QRCode中的傾偈錄音。她希望透過講自己的故事,令觀眾也能聯想到他們自己。我有點尷尬地聽著她說,因為其實我原來也是一直自以為了解,卻從來沒有細心聆聽的尋常男人,可能這是來自男性尊嚴所構成的某種不誠實。然後直到訪問結束,我才明白到,看一部關於女人的獨腳戲,為何亦會關男人事。

合作:當她看見他,他看見她時
雖然Jennifer加入《非常林奕華》已六年,但因為林奕華(Edward)主要時間都身在台灣,甚少看到Jennifer,直至疫情後才有較多溝通。真正展開合作的,是2021年的「Empty Theatre」項目:以空的觀眾席為主題,找來30個香港演員,每人發掘一段想對觀眾席說的話。Jennifer主動問Edward可否加入, Edward說早就為她預留一席:「我從來未看過她的獨腳戲,她怕我會設一些好壞判準,所以怕邀請我去看,而我其實只在乎真誠與否。我平日看舞臺劇一看到虛假的表演,就會感到很不自在,感覺像被穿上一副不合身的皮膚。而Jennifer,一開始我給她很多空間,也沒有給她時限去嘗試,只在休息時提了點意見。沒想到最後,我最喜歡的,就是她的那一段。因為她並不是在背台詞,她所做的就是她所想的,不是表演,而是一段發現自己的過程,每一秒都是真實的她。」這次,Edward終於真正看見了Jennifer。
他們之後常傾計,認不認真都有,每次都能更加認識對方多一點。有一晚,Edward拿出一個劇本來,說很適合Jennifer。這個劇本就是《女與兒》。當晚Jennifer看完劇本,雖然未能立即與自己聯繫起來,也沒想過將會跟Edward合作,只是當下心裡很想把這個故事演繹出來。直到「Empty Theatre」完成後,Edward構想為30位演員每人做一個獨立作品,當中就包括了Jennifer,「我好像一個裁縫,為不同的演員去做一件衫,例如我為何韻詩穿上了『賈寶玉』。認識一個人後我會想有什麼適合他,這個才是導與演員的真正關係。我從來不找人做群眾演員,因為台上每一人都是主角,由當年成團找來學生演員,到台上有張艾嘉和王耀慶,我都不會讓任何人覺得自己是配菜,我會安排一些事讓他們做,從觀眾的反應,他們就會知道自己是重要的。」《聊齋》之後,他認為明星巡演加上龐大製作,這種講故事模式已達到極致,失去了新鮮感,而在疫症之下,反而有機會還原基本步,以簡單且基本的製作來做舞臺劇,這時候他便想起了《女與兒》這個劇本,也想起了Jennifer。
這種合作,與Jennifer過往自編自導自演相當不同,以前是自述式的小品故事,但《女與兒》卻是翻譯劇本。Jennifer認為最有挑戰性的是與Edward合作,因為他絕不會照著劇本去演,不知兩人會否無法溝通或是起到其他化學作用,幸好Jennifer仍是充滿信心,「Edward很明白我,甚至比我自己更明白我自己,他擅長觀察別人,又很願意把他觀察到的坦白講你知。」平時的Jennifer很守衛自己的情感面,雖然在過往獨腳戲中都會表露自我,但其實她並不相信別人,所以一直自已執導,「合作做Empty Theatre時,是我最袒露的一次,Edward給我很多推動力,開啟我對自己創作的抑壓,沒有預期地講出了過往沒有講的故事來,所有事都自然流露,我從未試過這麼真誠地分享自己。甚至被自己的表現觸動到,原來與Edward合作能達到這個高度。」

排練:導與演的空間
這個合作如何開始?答案是由做第一張海報開始。團隊合作與巿場推廣整體地思考,二人亦參考了過往世界各地的表演,有的冷淡直述,有的則設計了很多劇場效果或燈光佈置。但這次香港版的《女與兒》,沒有外國劇院的資源,沒有著名舞台設計師的佈景,也沒有星級演員的名氣,一切都由Jennifer去帶動,讓觀眾從她身上,發掘這個故事可以得到的意義與現實。Edward會放心任Jennifer去嘗試,在劇本外尋找很多新的實驗機會,要令台上台下的人都覺得好玩,不想她照自己方法做,「導演就是要製造一個氣氛,令演員自行去探索,我想由舞蹈開始,先跟編舞家劃定一些路線,然後要演員去行,從這個過程去找出氛圍。」他要找的並非走進街市路線的那種氛圍,今次的另一個困難是,獨腳劇缺乏與其他演員之間的碰撞,所以Jennifer在台上要「搵啲嘢嚟做」,一般導演會或許會叫她在酒吧倒杯酒然後找張梳化坐下,但Edward卻要她原地跳三十下才講台詞。這種預備功夫,是傾向心理多於真實。「我會在她的門縫攝一些信,但不提醒她有信可取,讓她自行發現,亦至少有些心理準備。」
Jennifer好奇為何Edward會想她去演,他回答《女與兒》這故事要由一位nobody去講述,Jennifer很是認同。因為這個劇本就像平常在巴士站碰到一個人,他和你聊天,說著說著就把整個人生故事講了出來,你會為之驚訝,但每一件事又似曾相識。「越多時間接觸這個劇本,就越覺得與自己相似,並不是性格或遭遇,而是不停想在人生中找到事物來定義自己,但最終徒勞無功,一次又一次,甚至不知其實根本無法定義自己。」Nobody並非指任何人都可以,而是要有魅力地做自己,而Jennifer最好看的就是做自己,女主角不單像她,更跟身邊好多人一樣,這部劇殘酷地把現實的問題拋給觀眾。但Edward指大多數人進入劇場,就是不想面對現實,現實都已經令人疲累,進入劇場會想有人幫自己加油,藉以肯定自己的想法;或有人拍拍背安慰他們,覺得自己並不孤獨。「只有很少的戲劇會告訴你,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,這才是現實。」

寫實:通俗劇式扮演以外
但何謂寫實?Edward認為並非現實發生的事,而是現實對人的意義。烏克蘭戰爭每天都有人死去,但這些新聞對我們真的有影響嗎?我們會覺得需要對事件有感受,但其實又未必很有情緒,「現實這個詞會就只能通過每一個個體自己去界定,就算有人在你面前撞車死去,有些人也不會直面死亡,而是擰頭而去,這就是他的現實。又或許是拿起手機去影,或打電話說給丈夫知道,甚至馬上賣出手上的股票,或感嘆有故事可寫⋯⋯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現實,是無窮無盡的。所以寫實只能作為參考。這個劇本會引發我們如何去看這件事,以及如何影響我是什麼。」如何看待自己,是影響現實最重要的一環,這世界只有很少勝利者,而每一個人心裏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,而這部戲就是希望能對失敗者帶來衝擊,「因為他們永遠最想證明自己並非失敗者,但一去證明,他就失敗了,當他想證明自己是主動,卻把自己放在一個被動位置,他已經是主動地被動。現在我們常提及的網絡、虛擬、自我懷疑、失敗者這些詞,在三十年前沒有人使用,我覺得這是世界近年製造出來一種集體的人格原型,某程度上與經濟結構有很大關係。」
這種失敗者會嘗試把自己變成悲劇主角,卻不是透過偉大的戲劇,而是通俗劇。Edward指這是為甚麼我們喜歡看通俗戲中的誇張演技,「我們從小到大在家中已經在看戲,那部戲是一種家庭倫理大悲劇,大多數華人都在通俗劇氛圍中長大,習慣把自己的生活悲情誇大,那是我們在文化中不自覺所吸收的狀態,要求表達自我,自小學時扮了大人而不自知,到成為大人其實自己還是小朋友,所以他們情願去看通俗劇,因為他們熟悉。」通俗劇不能幫我們釐清現實,只會牽動你的情緒走入黑洞之中,而這些情緒對表演來說,是毀滅性的。所以如果《女與兒》演成通俗劇,情感洋溢就沒有意思了,Edward慨嘆很多戲劇還停留在冰山露出水面那一角,電視劇亦多數只在扮演,這種扮演很廉價,很虛偽。
所以Edward不去用情感或扮演填滿舞台,只要求演員經歷台上的時間是如何的過,亦給Jennifer最大的空間,令她由頭到尾都不需要演戲,只需要做事,「觀眾會看到她『做了很多事情』,唯一沒有做的就是演戲。希望透過看戲的過程會令觀眾明白,其實做人就是做戲,好好地做人就已經掌握了什麼是做戲,就會讓生活中看到的一切都變得不再一樣;這亦會間接提升我們的戲劇環境,因為觀眾會開始不想再看那些做戲的戲劇和電視劇,不會再認為有表情就是有戲。」寫實並非扮演,亦非去再現劇本那些場面與問題,而是去問這件事的價值和意義是甚麼,Jennifer給丈夫看《女與兒》這個劇本後,他馬上感到動搖,怕自已會否變成劇中的丈夫一樣,假如有一天老婆比我好的時候,那關係的平衡會否從此轉變。Jennifer認為這劇本會讓很多男士動搖,「或許人類本身就是這樣脆弱,所以我才覺得更加值得去做,因為單單是我丈夫的反思已經值回票價。所以這不單只是一個屬於女性的作品,反而男性看完會令他們感受更深,因為裏面所講述的,一般戲劇都不會提到;與女生相處時,男性不敢觸及的事情,尤其香港的男女關係中,女性越來越有實力,相處中女性越來越主導的關係,其實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影子,但我們都不敢講及。」

性別:放下角力,分享彼此
性別定型是《女與兒》所講述的主題,並不是要贊成或強調,而是有定型所以有這部戲。因為這就是社會現實:女是女、兒是兒,女與兒自小就被定型,互相鬥爭,破壞對方一切,同時成為彼此的苦難,這關係令這部戲成為悲劇,Edward認為女與兒的關係是不會停的,「我們很難擁有man and woman,大部分人都在你依賴我,我依賴你,很難成長為兩個獨立的個體,所以都很難為自己抉擇的對錯負起責任。現今世界越來越多人像這兩個人。女性覺得自己有本事,男性感到受威脅,於是各自都拿出一副面具,但各自也不想接受戴上面具的對方。這就是現實。」《女與兒》就像一個比喻,開場第一句:「第一眼見到佢,我嘅直覺話我知,我好憎呢個男人。」但最終為何反而愛上這個人?似乎從沒有搞得清楚過。人生的悲劇源自通俗劇的自我實現,人與人遇到磨擦時,就一起演出通俗劇,提高聲線講出:「你以後不要回來!」那些不能回頭的台詞,背後其實都並非真心話,只是模仿劇情,然後後悔,不斷跌入悲劇之中淪為受害者,「以受害者的視角去看,只會進入輪迴報仇的黑洞,因為有報不完的仇,只會進入Karma次中,再找不到自己更大的能力。」
這個Karma是世界性的,「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精神領袖,由近年世界局勢的大轉變可以看到,無論人民英雄或大國元首,今天的堅持明天又放棄,他們都沒有自己的原則或哲學,政治話言都只在服務經濟,懶理在苦難中的人,面講一套底講一套。」他們講出帶著光環的政治標題,而大眾只在複述他們的標題去說話,尋求認同並埋入人堆中不需思考,最終走向死胡同。「男性女性其實都是堆砌出來的:男人需要有夫綱,而女人需要獨立,但又並不是真正的獨立,我們都在說性別是一場政治,男性女性之間的角力,其實就是爭奪權力。」如何走出Karma?如果衝突是你一球我一球地碰撞,那我們要做相反的事:球來時就把球拍丟掉,「政治應是如何去創造一些事物,而非去爭奪,世界並不需要去爭奪,而是要創造理念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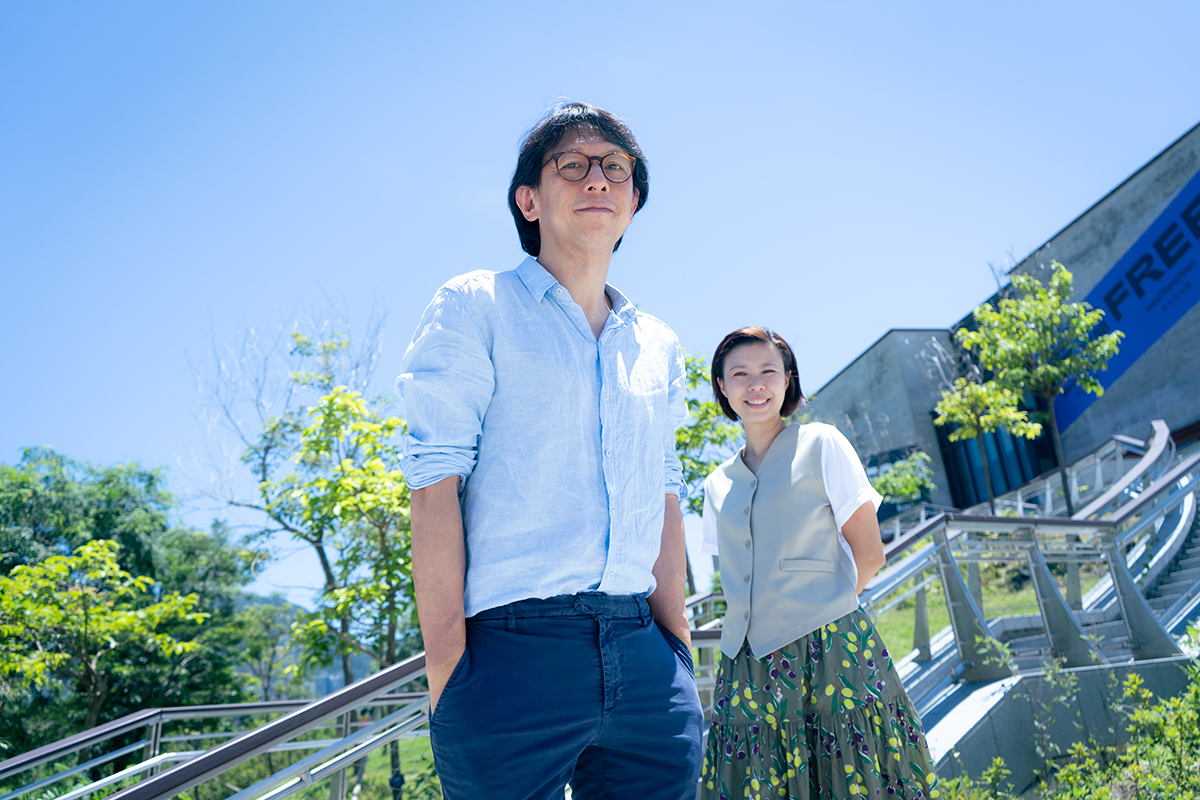
《女與兒》並非想成為帶領話語的媒體,不想觀眾跟從學話,反而是去製造空間,由Jennifer所展示的自己,如鏡一樣照射出觀眾的人生。每個人生都不同,Edward認為創作人需要有顆擺渡人的心,如果演出後能啟發他們如何與家人相處,反思對自己的期望,他覺得這已功德無量了。「『Tran-』這個字有過渡的意思,人生本來就是在不斷過渡,只不過家庭制度會令人以為是最安定的,但其實每一家庭都在經歷不同過渡。如果每個人從認識自己的角度出發,都回頭去看自己的遭遇,然後說他自已真正想說的話;只要家人可以放下面子,分享彼此的過渡經驗,不需強求表現體面的話,那就可以把牆打破,世界就會改變。」
PHOTO BY KAYAN WONG
